|
不久前,马库斯·吕佩尔茨、德国雾普塔大学艺术院校教授杨起受邀与中华艺术宫的负责人共同就“漫谈艺术与民族性、传统与当代”这一主题进行了 探讨。吕佩尔茨认为:在欧洲,艺术家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那些评判的标准都是由艺术家制定的。而今艺术家却时常成为政治或者非艺术 方面的“插图”,这是值得反思的。 中华艺术宫研讨会现场,左起:李磊、施大畏、马库斯·吕佩尔茨、杨起 莱纳·费廷1979年作品《凡·高和墙-太阳》 贝尔·恩德齐1979年作品《油菜田》 莎乐美1979年作品《Haematorrhoea》 马丁·基彭伯格1984年作品《两名无产积极女发明家在她们去发明家大会的路上》 沃纳·巴特那1982作品《请在晚上8点时醒来》(局部)
不久前,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漫谈艺术与民族性、传统与当代”的学术研讨会。德国前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院长、著名德国新表现主义艺 术家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uepertz)、德国艺术哲学博士、德国雾普塔大学艺术院校教授杨起等受邀与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副馆长李磊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吕佩尔茨认为:每 个艺术家都应秉承民族性的东西,只有在这种大的自己的环境下面实现自己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给其他人看到,这也是一种国际性。在欧洲,艺术家处于一个核心的 地位,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那些评判的标准都是由艺术家制定的。而今艺术家却时常成为政治或者非艺术方面的“插图”,这是值得反思的。 每个艺术家都应秉承民族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国际性 李磊(中华艺术宫副馆长: 我们知道马库斯·吕佩尔茨先生是当下艺术界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吕佩尔茨先生,这一段时间你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有什么基本的观感? 吕佩尔茨(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前院长: 从慕尼黑起飞到上海刚开始没有太多的陌生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能够看到和欧洲一样的建筑,和欧洲一样的汽车,中国也能够喝到卡布其诺和意式浓缩咖啡,然后我要回忆一下:对我来说中国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的是中国的长城,对我来说中国的长城类似于中国的巴洛克艺术,包括类似于中国的这些巴洛克音乐,这在欧洲人家可能还没有听到 过,然后我慢慢接触到了对欧洲来说中国深不可测的东西,当时是怀着欧洲人的那种神秘感解剖中国一样的,在北京经历了第一次的一些失望,中国的着装不是按照 中国人传统的方式着装的,穿的也是牛仔裤,很西化的一些。 但我为了参加中国的这次展览会,自己改了一个中式的长衫,看上去就像清朝的满洲人。但是奇怪的就是说街上的人反而觉得很怪,盯着我看。包括许多人北京人让小孩站在我旁边跟我合影,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交通拥堵,这就是艺术。 其实中国的许多艺术还是有很多的中国艺术家进行精心维护和保持的,包括书法、美妙的水墨画等。我来了几次以后,真正的感觉这里确实有中国的绘 画,包括一些中国的油画、丙烯画等等都有,对我来说这一切既新鲜,又是一种很熟悉的东西,我对此非常受到鼓舞和振奋。我也很想认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我 要把过去珍重的东西和当今的东西结合起来。今天我也跟施大畏馆长和杨先生说过,中国正走在路上。 我强调一下,每个艺术家都应秉承民族性的东西,其实每个艺术家都是在他所身处的环境、灯光、氛围当中进行他的艺术创作,只有在这种大的自己的环 境下面实现自己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给其他人看到,这也是一种国际性。所以,由此来说,中国的艺术对我来说并不是陌生,或者说虽然有点陌生但是还是有一种熟 悉感。 在艺术界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不但在中国、在欧洲也看到过,就是有一些美式的帝国主义倾向,踩扁别人彰显自己。所以看到带有英语名称标注的东西,我也开始觉得很可怕了。 我在1962年、1963年第一次在柏林看了美国的表现主义画展,当时不是那么的著名,并不是在柏林正宗的美术馆,而只是在一个艺术学院的画室 里面进行展览,对我来说当时是非常棒的经历。我看到了德·库宁等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大部分都是出自欧洲的。当时许多的美国画家,有一部分来自法国巴黎,他 们也是倾向以欧洲的艺术风格为导向,临摹抄袭了巴黎的风格。 在欧洲,艺术家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那些评判的标准都是由艺术家制定的。然后出现了先锋主义这种艺术。先锋主义、前进主 义颠覆了过去的阶层化的组织机构,它强调的是创意,它对创意要比艺术本身更加重视。先锋主义创造了一大批的“大师”,随后这些先锋主义在世界范围变得越来 越稀奇古怪了。先锋主义最高的那个峰值是在摄影界,其实摄影本身是有自己内在规律性的。而他们当时甚至想颠覆传统的作画,因为当时他们想通过摄影来把传统 的画家排挤掉,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做到这一步。但是这些摄影家尽管如此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包括在许多的博物馆、画廊当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这些人都是一些“教育家”,他们要强迫别人理解一些东西;也因为这些人都是“教育家”,所以其实从事的事跟艺术创作、绘画是不相关的,他们只想 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其他人。所以今天,我在中华艺术宫看到有许多的画,我觉得很鼓舞,在欧洲与此相反,很多关于照片的艺术已经把绘画的艺术给压倒了,在这儿 我看到很多绘画。在欧洲的一些大的美术展览会,尽量刻意回避一些传统的画,不管是双年展,或者是卡塞尔文献展,都是刻意地回避传统绘画。 策划一个展览,策展人在上面,艺术家在下面,策展人把艺术家应该得到的赞扬和名誉夺走了,所以基本上都是策划者永垂名史,艺术家成为政治或者非艺术方面的“插图”了。但其实绘画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上帝般的东西。 尽管如此,上帝般美妙的绘画也会被遗忘,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大师已经被忘记了。这些情况也会发生在大的画家身上。 造型艺术和创作者本身所受的教育程度、知识面,包括他自己对艺术倾向性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欧洲有一种很严重的混乱现象,即一些大的艺术家本身还 不会阅读。在德国诗歌已经死亡了。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来进行交流。以后结婚方面的事可能也要通过手机来进行了。这也是未来人们交际的一种现象。不过作 为造型艺术家来说,我以后还是有机会把我的作品呈现给世人,我很庆幸这一点。希望大家听到这一切不要特别的消极,这并不是特别消极,因为造型艺术永远是为 少数人打造的,我们现在已经被“民主化”所宠坏了,我们想要任何一个“被解放”的人,自然会有一种智力。 但在欧洲,所谓的智力、智商并不是在变多,而是在变少,所谓艺术“民主”已经变得非常无聊了,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娱乐泛滥的世界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这是我们大家需要进行应对和研究的问题。 东西方走到了一个殊途同归的交叉点 施大畏(中华艺术宫馆长: 当我们在多元文化的格局底下,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怎么国际化?又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国际的语境当中去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这就是我们当下要研究的课题。 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展览,就是德国表现主义、当代表现主义跟我们中国现在的一种新表现主义共同展出,思考表现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当中的共通点。 那天我跟杨起先生聊天,我看了吕佩尔茨先生的作品以后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他的语言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跟我们中国绘画当中的写意很相近。那么 是一种什么现象或者什么理论基础,把我们中华文明那么长时间的写意精神延续到今天,是什么支撑了我们的这种自信?西方的艺术家又怎么对待我们东方的艺术, 为何那么有兴趣地去研究它的神秘?我觉得这就变成我们当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画油画还是国画,共同研究的课题。 这个课题很大也很小,绘画很简单,就用你心里的感受,去表达一个世界,用自己的感受去感动他的观众,就这么简单。然而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写意艺术,为什么东方艺术,可以延续到今天?为什么到了今天又被别人关注?是什么东西支撑了我们? 不过,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人的基本价值就是一个“真”,一个“善”,一个“美”。 吕佩尔茨:正是这种基本价值倾向,把传统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在这个基础上,今天再进行一些发扬和变化。 在德国,纳粹花了12年把整个的德国文化体系摧毁了。到我这一辈,虽然要进行传统艺术的复兴工作,比如说造型艺术,但是整体来说在德国,倾向传统的东西容易被人们忘怀。 施大畏:传统是相对而言,对去年,前年说的事情是传统,对今天就是当下。当下的东西过两天又变成传统。不管从具像走到抽象还是抽象走到抽象,核心的问题就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这就是我理解的。 我跟杨起先生聊的时候,突然想起两个图象,一个是蒙克的《呐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八大山人,他的鸟的眼睛。他们两个人都表现自己的内心 世界。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艺术样式放在一起的时候,从图象当中我们完全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跟德国表现主义离得非常近,也就 是说在多元文化的格局底下,通过那么多年的文化演变,我们走到了一个殊途同归的交叉点,也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认识。 比如吕佩尔茨先生的东西,我能感受到他涌动的一种感受,我也理解他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反思。包括杨起先生给我的画册,我非常能理解中国艺术家走到世界的艺术领域中,他的一种探索,一种表达,他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坚守。 从这个角度讲,给我们的策展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怎么做好我们的展览?要不然我们这批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变成一种“插图”,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人有时候的一种困惑。 李磊:我们接下来听听杨起老师对这些方面的认识。杨起老师出生在中国,但是他在德国受了教育,而且是长期生活在德国创作和生活,他对这两种文化的昨天和今天,东方和西方等问题会有怎样的看法? 杨起(德国雾普塔大学艺术院校教授: 其实我第一感觉就是,不管是中国艺术家在中国,或者在德国都跟他生活 发生非常重要的联系,绘画是一种自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看绘画的话,我会首先问自己,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自我,你是谁,谁是你,你为 什么要这样画画,你的画到底跟别人有什么共通之处,或者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我始终是两国文化的旅行者,也不知道什么是尽头。我的感觉是不管中国人 还是德国人身份,都跟你艺术家的创作没有关系,你只要把自我的能动性调动出来,就能创造最好的艺术。所以我经常说我即便不在德国,我在内蒙古、尼泊尔等任 何一个国度,真心地做我的艺术,把自己最自由的释放点调动出来,就可以一直继续往前走。 李磊:杨起老师特别强调了艺术家自我感受和自我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说,正如施大畏馆长前面也谈到,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一 个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把个人内心当中最真实的部分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在不同地方的人,来看这件作品的时候,依然会感动,就像我们听德国的音乐、德国的戏 剧,我们会感动;反过来,我相信中国的一些艺术,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介绍给德国的人民,介绍给世界的人民他们也会感动。 我们接下来再问问吕佩尔茨先生,你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家,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常年的做院长,我们问一点小问题,你的一个私人问题,你是怎么样成为美术学院的院长,又怎么来当这个院长的?等会儿我们再听听施大畏馆长怎么来当这个馆长。 吕佩尔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是在30岁的时候成了教授,在卡尔斯鲁厄艺术学院做了14年的教授,然后调到杜塞尔多夫,博伊斯当时把杜塞尔多 夫美术学院搞砸了,当时的那些教授之间也有争吵等等,一切都不是很顺利。当时所有的教学人员和美术学院的老师都很混沌,人事方面很混乱,在棘手的情况下我 到了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任职。我当时的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当时我也是被视为一种“破坏者”,那时我们也有帮派、体系内斗很厉害。人们当时把我当作裁决人员 整顿这一切,幸好我当时有铁腕的手段。我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也做了约30年的院长,他们是每四年选一次新的院长,每四年都选我,而且是全票的。这就是我 学术方面的黄金时光,现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已经降级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怀念我的黄金30年时光。 当然,搞好一所院校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要靠整个学校的状况和同事的齐心协力。我一个人是做不了的。在我任院长期间,我们选教授的原则是选最好 的人员进来,这个原则一直坚持到我最后的任期。但是正如中国也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造型艺术方面,时间是有限的,年华是有限的。在我任期时,绘画和雕塑是 比较大的一块。我结束任期之后有许多的艺术家,基本上跟我是同龄的,也基本上结束了他们的工作生涯,而新的一代的人,不能取得很好的一致。 李磊:做一个美术馆,做一个美术学院都是非常不容易,确实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团结优秀的艺术家和员工。 杨起:所以在德国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艺术家都是个性比较强的,艺术家之间都比较独立,按照中国人说法谁也不买谁的账,都有理,在校园里面把 他们管起来,是需要非常强的能力的。吕佩尔茨做院长的时候,把世界很多艺术家,不光是德国本土的,包括国外的艺术家请来成为杜塞尔多夫的教授,这是他的能 力,他管理的天才。 在德国曾经出现自由艺术,自由艺术是德国现有的美术学院总的教育纲领,和民主、和德国的政治都有关系。有了自由艺术以后,德国各大美术领域的大学和学院,都是遵循这个纲领进行教学和创作。 它跟我们翻译出来的“自由”是不同的,它的意思是要调动艺术家和在校青年艺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还有传统艺术教育为基础,建立起个人艺术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在德国,在法国、英国等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到。 欢迎添加微信:zmkmsc加入古玩收藏交流QQ群(282603373),认识更多古玩收藏爱好者。 相关知识: 道光通宝 光绪元宝图片及价格 嘉庆通宝 顺治通宝 古钱币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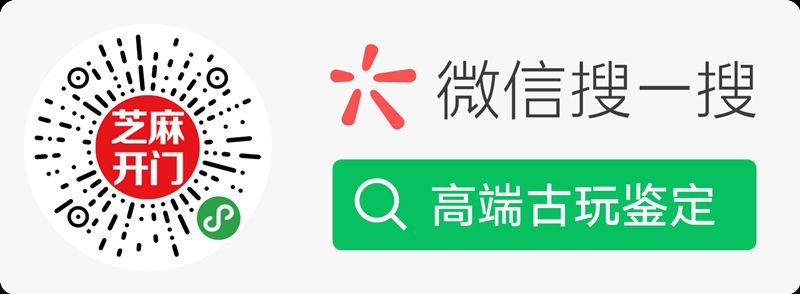
|



























关于吕佩尔茨:在欧洲艺术家处于核心地位是传统的评论